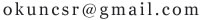《别跟自己过不去》(一) 一夫
(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是驻内蒙科尔沁草原地区一个步兵师的作战参谋。正是冬训阶段,我们作战部门挺忙活,早晨刚上班,科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任务,要我到离师部300公里以外的B团布置一项战备工作。
“路上要小心,千万注意安全,我看这天气要变呐,你到了B团一定要来个电话。” 草原冬天常有暴风雪,每次出门科长都是婆婆妈妈地嘱咐。
“要不,我把这个月的党费先交了吧,遗嘱就免了。”
“混小子,走你的吧!”科长笑着把我踹了出来。
我揉着屁股嘟囔:“哼,笑里藏脚!”
略做准备,我便开着科里的老爷车上路了,这是台老掉牙的北京212吉普,跑起来声音像拖拉机,可那时就这条件,不象现在,边防部队一律中高档越野车。去B团的那条路相当难走,就算每小时跑30公里,也得十个多小时。
刚开出师部大门,眼前就出现一道风景线——我们这些“生荒子”(即单身汉)公认的师部第一美女,通讯科的周洁在马路中央拦我的车,我故意来了个潇洒的停车动作。
她背了个军用挎包,娉婷地走近车门。
“你去B团?”
“是啊。”
“我跟你们科长说了,搭你的车去B团。”
虽然她说话时小脸儿冷得像挂着冰碴,我心里却乐得捏一把能挤出糖水儿来,有个大美女相伴,这十多个小时可不寂寞喽。脸上却装得无所谓的样子,开了前边车门。
“上来吧。”
周洁对我的殷勤置之不理,反倒拉开后车门上了车。
她对我这个态度是有原因的。那是一个月前,她刚从院校毕业分到我们师。一天中午在机关食堂,我们司令部七、八个“生荒子”凑在一桌,一边吃饭一边闲聊。突然,桌对面我的老乡陈龙像被点了穴道似的楞在那,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面,人眼瞪出了牛眼样子,张着嘴露出一口没咽下去的大米饭。
我从桌下踢了他一脚:“喂,大龙,你哪根筋不对?”
大龙回过神来,用他那肥沃的双下颌向前点了点。这个动作引起大家的注意,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一个年轻的女军官正端着饭盒走到离我们不远的餐桌前坐下。怪不得大龙那副德行,她长得的确可圈可点,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里对女人容貌的精粹描写太多了,用在她身上都挺合适,我也就不再出力不讨好了,只告诉你们,我当时看见她的第一联想,那就是草原上的梅花鹿——小梅花鹿,美丽的身姿,挺直的颈项,晶莹剔透,天真、纯洁的大眼睛,对,就是这个感觉!
“哇——呀呀,真不是盖的!”
“你看看人家,比卫生科那些强多了!”
“哪个科的,哪个科的?”
“听说通讯科今天分来个新毕业的干部,八成是她吧。”
这帮哥们儿眼珠冒火星子,嘴里喷饭粒子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而且嗓门越来越高,也不怕人家听见。
我们师部也有女兵和女军官,可都是师卫生科的,而卫生科和师部又不住在一起,一年也见不着她们几次。为了和人家套近乎,这帮“生荒子”有事没事总爱找个头痛脑热的借口往卫生科跑,如今身边来了个美女,焉有不兴奋之理?
“喂喂,肃静!肃静!本人发表一项重要提议,哪位和我赌,现在谁敢过去约她晚上出去吃饭,他一个月的饭票我包了!”军务科的包尔图大声宣布。
大家你推我,我搡你,没人敢出头,却又不甘显出自惭形秽,“嘁,嘁”地嘴里出声,屁股不动,脸上一副不屑。
眼看美女就快吃完了,圆头圆脑的大龙给我使了个暧昧的眼色:“阿米尔——上!”这是我们之间的黑话,援引电影“冰山上的来客”。
我环视四周,自我感觉各方面比他们优越点,胆子比他们肥大点,便站了起来:“看来,这火力侦查的任务只有本人去完成了。”
大家顿时静下来,用无比崇拜的目光注视着我。其实,我往她桌子走的那几步,却也有点慷慨赴刑场的感觉。
食堂就餐的人本来就不多,这时她的桌上只她一人。我端着饭盒走过去,坐到她的对面,挤出一脸灿烂:“刚分来的?”
“嗯。”
“哪个科的?”
“通讯科。”
她脸都没抬,那语气让人冷得毫毛倒竖,我这才感到事情不妙,我们刚才说的话许是让她听去了,还没交火,情报就泄露,这仗还怎么打?不过现在铩羽而归也太没面子了,只好硬撑下去。
“呵,刚来的,那咱得欢迎新战友是不是,好!我这老兵今天尽地主之谊,晚上请你吃饭,城里最好的饭店,怎么样?”
“请客?最好的饭店?把钱拿出来吧!”
“钱?钱不是问题,老资格嘛,工资比你高!”我慷而慨之地把这个月刚发的工资全部拍在桌子上,隐约觉得掉进了陷阱。
她拿了饭盒起身,顺便把钱收了去,来到我们桌前,也学我的样子,把钱往桌上一拍:“这位英雄说了,今晚他请你们吃饭,最好的饭店!”说罢扬长而去,留下满堂哄笑。
……三天前下了一场雪,我们驻地的这个小城像被一枝巨大的画笔蘸着白颜料饱满地涂了一笔,白的街道、白的房顶、白的树枝,穿行其间像进入虚幻的童话世界。
“喂,你去B团干什么呀?” 我从车上的后视镜看着她问道。
“有任务。”
“去过吗?”
“没有。”
“这个时候去B团不是闹着玩儿的,路可不好走啊。”
“你去得,别人就去不得!”
“我说小丫头,本人欠你钱没还吗?”
“不欠!”
“不欠你钱,说话火药味儿别那么足好不好,本人可不是坏分子,阶级敌人什么的,好歹也是老兵了不是?”
“谁是小丫头,谁是小丫头!老兵?老兵有你们那样吗,为老不尊!哼,没来时,原本想向你们老同志好好学点东西,学什么呀,学你们那天那副德行?”
这一顿机关炮连续射,弄得我一时无法招架,只好采取以退为进的战术。
“好啦,好啦,我现在谨代表全师部的老同志,全心全意地,严肃认真地,一丝不苟地向你道歉:sorry ! sorry!”
后视镜里,看到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瞪了我一眼,靳靳鼻子:“哼,这还差不多!”
说话间,车出了城区,进入科尔沁大草原,我们的行车路线是沿洮儿河以东,绰儿河以西的中间地带,也是科尔沁草原和大兴安岭的交界处,穿过索仑一直向西北方向行进。说是有路,其实根本不是路,只是车走多了,压出的一条稍微平一点的地面,三天前的一场雪把路面结结实实地盖住,经车轮一压,滑得连个跳蚤也站不住,使本来就凹凸不平的路面更难行走了。去B团先要走一段草原,然后进入丘陵地带,也就是大兴安岭脚下,那是无人区。B团流传一个典故,一个连队司务长开车到师部拉粮食,回去的路上掉了一袋白面,一个月后回去找,仍然好好地摆在路中央。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那儿是绝对实现了。
进入草原腹地,放眼望去,辽阔的科尔沁大草原在皑皑冰雪下显得更加美丽妖娆,远处,覆盖着白雪的蒙古包,像镶嵌在银白色地毯上的一颗颗珍珠,在阳光照耀下闪射着晶莹的光芒。置身其间,感觉天是那么高,地是那么广,再把感觉伸延开去,空间就变得无边无际,而回头看看跟我在同一个村子里忙活的人类,却显得那么渺小。
车摇晃颠簸着,老牛似地爬行。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周洁被颠得像簸箕里的黄豆,呲牙咧嘴,没一刻安稳,便把车停了:“到前面坐吧,路长着呢,这么颠下去,身上哪个零件颠丢了,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可配不上哦!”
“哼,过去就过去,看你能怎样!”她撇着小嘴生气的样子真好看。
为了改善气氛,我没话找话:“你刚毕业,还没下过基层吧,其实,基层也挺有意思的。有一次,B团一个连队养的老母猪丢了,找了两天没找着。一个礼拜后它自己哼哼唧唧地回来,没多久就生了一窝猪崽儿,总共八只,你猜怎么了?八只猪崽清一色长着獠牙,从来不躺着睡,趴着睡。原来,这老母猪生活作风有问题,私自跟野猪搞上了,哈哈!”
效果不佳——周洁没笑,乜我一眼不知嘟哝一句什么,我没听清。
继续努力——我接着白乎:“有一次,我跟首长到B团一个连队蹲点,跟连队干部吃第一顿饭,第一道菜上来一盘凉粉,连长为了向我们表示连队农副业生产搞得好,客气地说:首长,来吃吃,这凉粉儿是我们连队自己拉的。又指着厨房说:看见没?就在那儿拉,绝对新鲜,现吃现拉,吃多少拉多少。”
“咯咯咯——咯咯咯——现吃现拉!哎哟,真逗死了!”她终于笑了,而且笑弯了腰,那银铃般的笑声盖过了发动机的牛吼,脸上一对儿笑酒窝让我看着了迷。
笑声倏然而止:“你为什么不笑?”她忽然绷着脸问。
“我,也需要笑吗?那好,嘿嘿嘿——!”我挤出一脸狰狞。
“你这人怎么这样?”她抿嘴笑问。
“怎么样啊?”
“总没正经的。”
“我呀,就这样,除了师长、政委,全师谁的玩笑我不敢开?我上‘肚里蹲’大学时——”
“什么是‘肚里蹲’啊?”她问。
“哦,就是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妈十月怀胎时,特爱听相声,天天听,本人在‘肚里蹲’受过这样高等教育,所以嘛,一出来就成了这副德行。话说回来,驻守边疆够苦的了,再成天道貌岸然的,累也累死啦。不过,你可别学我,不然,包你成为失足青年还自我感觉良好。”
“臭美,谁会学你呀!哎,你来边防几年了?”
“不多,八年。不过,说实在的,咱们在机关算什么苦,基层那才叫苦呐。B团的秦副团长,两口子是北京人,在这儿生了孩子,孩子长到四岁,带回北京探家,孩子见人家吃雪糕,楞是不认识,问妈妈他们吃的是什么,你说当妈的是什么心情?一个边防哨所的战士,当兵三年没进过城,好不容易班长给了假,进城照个相片,临行的头天晚上激动得一夜没睡。”
“他们太不容易了,我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她感慨地说。
……
车进入了丘陵地带,路更难行了。走到地势较高的地方,远眺开去,一座座雪白的小山蜿蜒起伏,伸延到天边,那圆弧形的山顶,在眼前横向画出无数优美的曲线,像忽然凝固下来的海面,我们的吉普车就似一艘小船,在银色的波涛中行进。
蓦地,一群生着褐色羽毛,比鸡小、比鸟大的动物从路旁的红柳棵子中窜出,旁若无人地从车前跑过。
别跟自己过不去txt全集下载
别跟自己过不去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百度网盘,点击免费下载:内容预览:别跟自己过不去作者:我是李明泽黑子更新时间2008-1-14 17:45:00 字数:649 风弱,叶乱。说说黑子吧。黑子从生到这个世界就没有名字,因为长的黑,所以大家习惯叫他黑子。十三岁的黑子是个小偷。他是顶着太阳在教室被...
别跟自己过不去电子书txt全集下载
别跟自己过不去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百度网盘,点击免费下载:内容预览:风弱,叶乱。说说黑子吧。黑子从生到这个世界就没有名字,因为长的黑,所以大家习惯叫他黑子。十三岁的黑子是个小偷。他是顶着太阳在教室被老师赶出校门的,老师嫌的给学校丢脸!他是顶着太阳在闹市区被保安群殴的,店主嫌他...
别跟自己过不去
静下心来,细细地想,人这一辈子确实挺不容易,要走多少路,要经多少事,要面对多少选择,不可能总是春风得意一帆风顺,肯定会有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说不定哪一天倒霉的事,不顺心的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这时,就得想开点,平淡地面对生活,多劝劝自己,别跟自己过不去。年轻的时候,心高气傲,...
读书笔记 | 《别跟自己过不去》
《别跟自己过不去》以心理学为基础,以理论与故事相结合的形式,将哲理蕴含于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中,并配以画龙点睛的感悟,用平实质朴的语言,教导读者如何在忙碌的生活状态下静心审视和沉淀自己,以此重新发现生活的美好,解脱心灵、善待自我,进而以全新的状态和面貌前行! 不强求,不苛责,不执迷,不怯懦,永远想做就做,永...
别跟自己过不去是什么意思
别跟自己过不去 善待自己,爱惜自己 自己都不爱自己就没人爱自己了 洒脱一些过得好 放开心享受生活拥抱幸福 珍惜可以珍惜的,摒弃可以放下的 人生苦短,不必计较太多
别为打碎的镜子哭泣,别跟自己过不去什么意思
不要过分纠结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别为打碎的镜子哭泣,别跟自己过不去意思为,不要过分纠结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打碎的镜子无法复原,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让自己陷入负面情绪中,影响自己的心情和生活。
别跟自己过不去编辑推荐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往往不是因为得到的少而感到不快乐,而是由于欲望过多而产生困扰。快乐的秘诀并不在于物质的丰富,而是对欲望的适度掌控。别与自己过不去,这是一种内心释放,让我们能从容地追求自我,珍视生活。在闲暇时,听音乐以放松心情;在烦躁时,做运动以释放压力;在得意时,保持平静以修炼...
千万别跟自己过不去
要知道,世事犹如书籍,一页一页被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莎士比亚曾说:“向前看,不要回头,只要你勇于面对,抬起头来就会发现,此刻阴霾不过是短暂的雨季”。书要向后翻,人要向前看。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能治好人世间的一切痛苦。所以千万别跟自己过不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别跟自己过不去的经典语录
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别流泪,别人会笑。别低头,皇冠会掉。
本能2:为什么我们总跟自己过不去图书信息
《本能2:为什么我们总跟自己过不去》这本书由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首版时间定于2010年10月11日。这本书的外文书名被命名为《Bozo Sapiens:Why to Err is Human》,强调了人类在犯错过程中的本质。它以平装形式呈现,包含312页的内容,语言使用简体中文,开本尺寸为32开。ISBN号码为9787508623146...